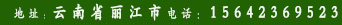|
白癜风初期症状有哪些 http://m.39.net/pf/a_6308377.html 五月的风早已不复清凉。夏还未至,却有了些铄石流金的滋味。一学年即将走到末尾,我们与哲学门的相识又多了一年。走出西门,穿过条条街道,我们来到承泽园一处单元楼下,期待着与在家等候我们的张翼星先生进行交流与畅谈,想象着与哲学门相识几十年的先生,又有怎样的体悟与指点呢? 博外而精内,情深而志笃 先生求学时即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后又在北大哲学系教研室任职,如今两鬓已斑白,但对于教育的热忱、对于学校的牵挂并未随时光流逝而改变。面对围坐一圈的大一同学,先生细细地问我们选了些什么课、对于北大的学术氛围感受如何,了解我们的体悟与困惑,言语中满含关切。 “作为哲学系的学生一定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要涉猎,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于己身。”先生十分认同蔡元培老校长“文理沟通”的教育理念,认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是一个博与专的关系,要在学问上有很高的建树,成为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二者缺一不可。先生用了胡适的说法来举例:“学问犹如金字塔,要能广大才能高。金字塔必须底子厚才能上得去。如果学问就像一张薄纸,轻飘飘的,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是很浅,那你就很难深入。但是如果只讲‘专’就好像一个电线杆子,也是立不住的,经不起风吹。” 对通识教育的重视与先生早年的经历有关,先生上学的时候,学校学习的是苏联的教育模式,一昧注重培养专才。一个系分十个教研室,每个教研室专攻一个领域,彼此间相互隔绝。这种教育模式导致研究哲学史的人不懂哲学原理,研究哲学原理的人不通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不懂西方哲学,这是很窄的“专”,并不利于学问精进。同时先生也指出,通识教育不仅要让学生丰富所知,也要提高课程质量、对课程进行全面的规划,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 为这个民族培养一批又一批大思想家、大科学家是蔡元培校长设立北京大学的初心。“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论诸理而尤贵达于事。”如何平衡博与专、广与深,是我们要不断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君子之学,博于外而尤贵精于内,论诸理而尤贵达于事。 ——[明]王廷相 莫任光阴逝,青春读书时 时间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珍贵的,但是在同一段时光中每个人的选择或有不同。于先生而言,如果时间的指针能够倒退到风华正茂的大学时代,他会选择拼命读书不负这段自由而美好的时光。先生上学的时候赶上政治运动,在劳作和批斗中度过了大学时光,他一直引以为憾,也勉励我们我要多花时间在读书上。大学时间安排比较自由,且少有杂事打扰,可能是我们能够最能够潜心读书的时候。要利用好四年时光,才不枉来北大一遭。 谈到书本的择选,先生认为还是以读原著为主。同时读书的时候也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对于比较困难的文本一定要反复阅读,不一定要逐字详解,比如读黑格尔的书,就不能一下就要求每句话都读懂,而是要先把握文本的大致内容和基本思路,比如涉及哪些问题、使用哪些概念、要解决哪些问题、留下了什么问题。读书要有自己的见解,善于独立思考。阅读有益于治学,在阅读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问题,便有兴趣继续做学问;做学问入迷了,就会手不释卷。 读书对于哲学系学生来说是基本功,先生举了他的学长——李泽厚先生的例子,李泽厚先生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整天呆在图书馆里自己读书思考、查找资料,上课时便觉老师给同学讲得浅了。虽然总是翘课,却依然在哲学研究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时间终将淘洗所有的浮皮潦草,要么乘着浪花随波逐流,要么深扎水中成为中流里的砥柱。先生多次提醒我们不要虚度宝贵的大学时光。忆起往事,先生不禁仰面叹道:“可是宝贵的时间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一声隔了多少往昔与旧事,重重地砸在我们心间。 先生与同学们交流 勤谨和缓治学,健康规律生活 在大学生活之中,先生特别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提出了建议。他讲到从前的胡适先生用“勤谨和缓”来说明治学的态度: “勤”——无论是多高天赋的人,都需要做到勤奋; “谨”——做学问要保持着严谨的态度,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切不可说大话、空话; “和”——做学问要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在学问中不能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情绪,而是要保持一种宽阔的胸怀气度,对各家的观点都多加包容; “缓”——切不可随当下浮躁的不正之风,急于发文章,甚至进行抄袭、剽窃,而是要将功夫做扎实。 先生将此言娓娓道来之时,声音徐缓而深切,似为只言片语难承殷殷之意。先生语中,不乏对当下学术界的关切与担忧,但更多的是对我们的满怀期望,希望平正的学术之风能够沿袭下来。 而对于我们这一众本科生,“勤谨和缓”的研究方法首先回归到了先生所说的读原著,要扎扎实实地将原著啃下来。先生还提及我们应当学好外语,例如在学好英语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接触以英语为写作语言的名著,这对我们的知识提高无疑是大有裨益。另外,要多向有学识的老师提问、交流,不仅哲学系中就有许多学术做的很好的教授,我们还同样可以与外系的教授进行交流,这些都将让我们在修学过程中受益匪浅。 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大致可以从先生的言语中感受到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上确由了“勤谨和缓”之法。 比如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仅有在中国的这一支发展,实际上在西欧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发展方向,而这也正是先生曾经研习最多的领域。先生并不因为哪一系的研究炙手可热而去研习,而是真正从自身对学问的认知出发,研究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问,这一点着实令人敬佩。不仅仅是研究领域,先生对于许多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教育问题都有着自己的思考与理解,例如马克思主义作为专业学习和作为政治课之间的关系,政治课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真正能够让同学们体认到马克思主义,言语中透着热爱与恳切。先生为我们打破了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印象,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学习、阅读中慢慢体会,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先生与同学们交流 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不仅仅表现在学术方面,还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提出了建议。例如,先生特别提到了锻炼身体。他回看自己的生活经历,深感生命无常,因此我们更要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与生命,让生活过的更加有质量。先生还提到我们的生活作息问题,建议我们应当按照生物钟生活,在学习的时候集中精力,提高效率;在需要休息的时候正常休息,这样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同时,同学们还要注意饮食的规律,不要暴饮暴食,注意这些细节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十分有益的。在这样好似家常的聊天之中,先生已经不仅仅是一位可敬的学者,此时更像是一位对我们叮嘱再三、放心不下的长辈。 我们从学问的深刻中走过,又感受到了学问之外的温暖,这次与先生的交谈,确实不乏厚度与温度。 太阳渐渐落了下来,厚重而温馨的气息在小小的屋子里凝聚又散去,我们起身向先生道别,将椅子摆回原位,一如来时。先生热情地送我们到楼下,挥手目送我们离开。我们也依依不舍的向先生挥手道别,心中感怀于先生的教诲与关怀。 绿树浓荫夏日长,何以消夏?一捧书卷,沉李浮瓜。 张翼星教授是我们曾多次拜访的一位先生,每次与先生的交谈总让人受益匪浅,可戳阅读原文了解往年访谈记录。 供稿丨哲学系实践部李洁睿田中慧 编辑丨孙安妮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xcyouhuo.com/qszb/10907.html |
哲学middot实践曾攀岩嶅挂星
发布时间:2020-11-29 16:59:01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男子沈阳世博园攀岩撞铁柱瘫痪世博园赔6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